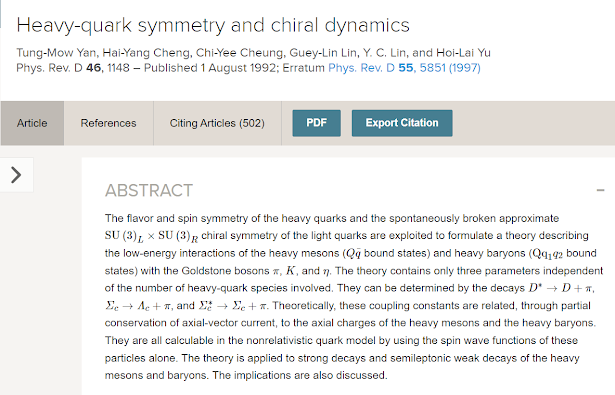我很喜歡這段小文字:“它是一種令人再三成癮的幻想,因為它會反身過來,將我們避之不及的現實改頭換面。其它的方式,像是性、迷幻藥、休閒、嗜好等等,相較之下顯得短促無味。”
這是一本關於數學家 Paul Edios 的小書《不只一點瘋狂》中第二章引用數學家 Gian-Carlo Rota 的一段話,講的是當數學家證明出一個定理時的那種強烈且持久的喜樂。我覺得對於理論物理的研究亦然。
我過去的專長是高能物理(high energy physics),或者叫粒子物理(particle
physics)。物理本來就是個小學門,高能物理更是是小學門中的一個小次領域。在我拿學位時,高能物理學家在整個物理界只占剛過二位數的百分比,現在可能是個位數。所以自稱小小學門也不算虛懷謙沖,比之於生醫或電資可能連零頭的零頭也不到。
但是高能物理在上世紀持續綻放異彩如花火,得物理諾貝獎的工作遠超過學門人數的比例。所以在上世紀的下半段還是有人前撲後繼的爭看落日餘暉而投入。
做理論物理的與做數學的有類似的,也有互異的。不同的是物理與真實的世界要能相對照,而數學儘可在抽象的世界中神遊太虛;但是二者在心智活力中的起疑、思索、困頓終而豁然開朗如“錦江春色來天地”的舒展則一。
我記得那天天色已經有點晚了。顏東茂是我物理系的大學長,在高能物理的領域已不是僅用 well-established 可以形容的—他還在工作,而粒子物理的教科書上卻早已有他的名字:Drell-Yan process。
他那時在中研院物理所訪問,我順道請他到系上演講。演講完後,照例請他到辦公室談談物理,這是邀請者的特權。我問他最近做什麼?他說做重夸克(heavy quark)物理。
組成世界的基本粒子中有夸克、電子、光子等。夸克至今知道的有6種:up、down、strange、charm、bottom、top。前三者質量較輕,如果略去質量不計,系統具有手徵對稱性(chiral symmetry)。後三者較重,就是重夸克,重夸克另有重夸克對稱性(heavy quark symmetry)。當時由於加速器能量漸增,這些較重粒子的發現以及對其性質的探索是當時的熱門議題。
顏在白板上寫下他用電流代數(current algebra)計算的初步構想用以研究輕、重夸克物理。電流代數利用對稱性來計算各種物理量之間的關係,是高能物理發展初期重要的工具之一。
顏的問題是雖然重夸克對稱性可以簡化一些計算,但是計算的結果會包含許多未知的參數。當然參數可以用實驗數據來擬合(fit),但是一個物理模型/理論含有多個參數就不是一個好的模型/理論,這是任一個做理論的人都知道的事,這令他苦惱。
顏在白板上寫完式子後,兩個人不發一語、注視著白板上的式子苦思。有一陣子之後,落日餘暉從窗子斜穿在白板上,才發現天色已晚,辦公室還沒開燈呢!
我開了燈,房間為之一亮。突然腦海中也同時靈光乍現,Eureka! 一下子腦嗎啡因滿滿的。
那些眾多的參數可以使用手徵對稱大部份消去,只留下一個參數!而即使基礎如量子電動力學(QED;Quantum Electrodynamics)理論,也尚有一個如精細結構常數(fine
structure constant)的參數!
我隨及建議顏不要以電流代數這種稍為古典的方式來表述,改為在教科書更為通行的 Lagrangian 來建構基礎模型。這卻是出於本能了。我的博士論文便是以 Chiral Lagrangian 為主題的(啊,這不是國家機密,網路上可以查得到的!)。
當下兩人決定要啟動研究計畫。幾天後我到中研院物理所參加例行性的演講聚會時,陸續有幾位研究員表達加入合作的意願。團隊一下子膨脹至6個人。這6個人的 last name 分別以Y、C、L三個字起頭,所以我們群組自稱(YCL)^2,YCL 又恰好是我英文名字的頭文字,有點巧。
以往從事理論物理的研究,合作人數最多就3、4個。6個人合作是稍為多了些,但是人多有人多的好處,驗算快,也可以同時展開多條戰線。
就這樣的陸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幾年前,為了紀念當年的合作,又新發表了一篇。這時顏早已退休了,而我也已移往產業界工作滿20年了。我必須承認,在後幾篇的發表中,我的貢獻遠遠不如合作夥伴們。
那一系列文章發表多年後,為了商務到矽谷拜訪客戶,自然的踅到史丹福的書店,不由得翻起相近領域的書。有一本 Cambridge monograph 的《Heavy
quark physics》在我們發表的相關領域章節中引用了多篇我們的文章,這才意識到當年的工作也總算是留下了身影。
今天收到了 Academia 的通知,“有人引用你的論文…”。隨手點了進去,那篇奠基的文章引用數已滿1000了!
引用數在每個學門的意義不太一樣的。在高能物理領域享大名的費因曼最早關於量子電腦文章的引用數早已破萬,這是開闢一方天地的工作。但是另一個也是國人衆所周知的工作—丁肇中和 Burton Richter 發現 J/ 粒子的諾貝爾獎得獎作品引用數分別為
254 和 817,這是與我們相同的次領域。
粒子的諾貝爾獎得獎作品引用數分別為
254 和 817,這是與我們相同的次領域。
當學生時不明瞭為什麼發明一項方法或者儀器可以得諾貝爾獎,譬如1922年化學諾貝獎的質譜儀 (mass spectrometer),畢竟這和大自然的奧義沒有直接關係。但是自質譜儀發明之後,有6、7個物理或化學諾爾獎是利用質譜儀做的工作。
又譬如 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在經歷過疫情之後大家應該都熟悉了,它在 1985 與1993 分別得了化學諾爾獎之後,又助攻了尼安德塔人的基因組分析,得了去年的生醫諾貝爾獎。工具的發明是自然奧義發現的支柱,而且可以重複得分,是以重要。
我們工作的意義也在此:當強作用的基礎理論 QCD (Quantum Chromodynamics) 難以直接用之於計算真實世界粒子之間的作用時,我們的模型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工具,用以處理含各種夸克粒子之間的強、電磁、弱作用等。
能當做後學者做研究的墊腳石,心中可樂了!而做理論的比做實驗的幸運些,只要心中的那塊白板還在,這種靈光乍現的樂趣就可以持續。